離柴靜《穹頂之下》的發(fā)布已超過30個小時,過億點擊率之下各種聲浪仍在不停地席卷、翻騰,不為刷屏、不為學(xué)術(shù),只因作為一個社會學(xué)學(xué)者,此時應(yīng)該,也必須要說點什么。
老實說柴靜此次放大招冒著相當(dāng)大的風(fēng)險,首先是冒非專業(yè)的風(fēng)險,這對曾經(jīng)的資深記者似乎不是問題,但是視頻橫跨環(huán)科、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、歷史和政治多個專業(yè)領(lǐng)域,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心態(tài)很難拿捏;其次冒被體制內(nèi)極權(quán)抨擊的風(fēng)險,她在臺上每一次的踱步其實都在涉水,每一句看似的輕描淡寫都可能被大做文章,甚至關(guān)聯(lián)政治;再者,大家都看到了,冒被網(wǎng)絡(luò)輿論裹挾的風(fēng)險,揭隱私的、翻舊帳的、編故事的,不要說柴靜本人及團(tuán)隊,就連昨晚上力挺的今天都有可能倒戈。
但是她仍然這么驚天動地地發(fā)聲了,以一個自由人的身分,極其個體化地發(fā)聲了。通過環(huán)境事件發(fā)出個體的聲音,在歷史上、在全球并不鮮見,西方20世紀(jì)許多著名的公眾參與事件很多都源于環(huán)境維權(quán)。在忍無可忍的華北天空下,柴靜只是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了要發(fā)聲、要捍衛(wèi),哪怕僅僅是出于保護(hù)女兒的沖動。她的發(fā)聲首先想到的是剝洋蔥般地呈現(xiàn),顧不上邏輯、顧不上數(shù)據(jù)來源是否可靠、顧不上可能會觸動多少權(quán)威的神經(jīng),她就是要表達(dá)、要參與、要發(fā)聲,她想破那個“有義務(wù)沒權(quán)利”的金句。
不能不說這樣的個體化發(fā)聲如果不是來自明星或公眾人物,動用再多的經(jīng)費(fèi)、依靠再多的人脈,在自媒體時代仍然翻不了幾朵浪花。如果不是柴靜,還要不要發(fā)聲,或者說柴靜之后,每個被剛剛喚醒的個體要不要發(fā)聲?這其實由不得制度,也由不得時代,這是潛藏在每個個體里面的那些熱血、那些良知、那些公民性。
也許會有人會說只能依靠個體化發(fā)聲是悲哀的。社會原本就是來自個體,好的社會就是為每一個個體服務(wù),個體還有機(jī)會發(fā)聲,還能真心說出自己想說的話,每個個體還有他(她)合法化的發(fā)聲途徑,能夠體驗自治、感受參與的美好,雖不一定足夠,但仍心存感激。所有個體化的、真誠的、理性的和持續(xù)的發(fā)聲,聚合起來的公眾參與就撬動了社會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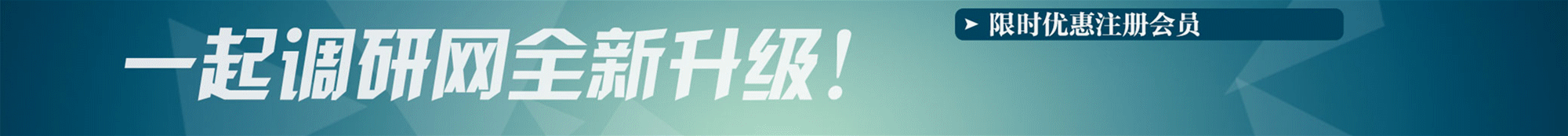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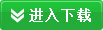



 一起調(diào)研網(wǎng)新浪微博
一起調(diào)研網(wǎng)新浪微博
 一起調(diào)研網(wǎng)騰訊微博
一起調(diào)研網(wǎng)騰訊微博
